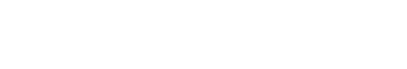搜索
-
×
- 首页
-
本系简介
-
×
-
概述
-
历史沿革
-
机构设置
-
规章制度
-
联系我们
-
师资队伍
-
×
-
专职教师
-
兼职教师
-
博士后
-
教学教研
讲座回顾| 王子今:从战国到秦汉——天地一大变局
4月17日下午,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王子今受邀在闵行校区人文楼1306会议室发表题为“从战国到秦汉——天地一大变局”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我系章义和教授主持,四十余位系内外师生参与活动。

王子今教授本次讲座主要从“天地间一大变局”、“‘天下一统’与‘天下一致’”、“秦赵之坑若循环”、“文化演进与知识人的活跃表演”、“秦统一进程中的文化理念变化”、“技术发明与生产进步”六个方面展开。讲座伊始,主讲人开宗明义地指出,由司马迁所提出的“周秦之间”概念应当值得学界所重视,因为这一时段既是中国历史思想文化创新最突出的时代,也是生产力跃进与技术发明丰收的时代。对于周秦之间重要历史“变局”的考察,除了关注政治形式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以外,也应注意到时人的天下意识、海洋意识、地理格局与文化演进也都具有新的时代风格。

“天下”的说法最早见于《尚书》,“天下”的观念从产生之初就与追求和认同统一的观念相联系。主讲人指出,在“天下”意识的普及同时,许多思想家都相应提出了以“一”对应“天下”概念的主张。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子》中出现“天下”一词凡267次,以强权和暴力夺取并控制“天下”的主张,对秦政有直接的影响。而在汉代的政治语言习惯中,“天下一统”又称“海内一统”,“海内”与“天下”的这种对应关系,体现出时人对“海洋”的关注,是秦汉时期天下观变化的重要表现之一。伴随着“天下一统”观念的流行,“天下一致”这一出于追求思想文化同归目的的观念也随着兴起,“天下一家”的概念进而成为汉代重要的政治话语之一。为了避免“天下一家”之说成为以宗法为基础的极端政治控制,“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的说法也应运而生,体现了新的以“天下”为视域,以“天下”为基点,以“天下”为对象的政治理念。这种“不私一姓”的主张,表现出涉及总体社会格局的觉醒。
在战争史方面,主讲人指出战国时期秦将白起的“长平之坑”与秦汉之际项羽的“新安之坑”是中国古代战争中最惨烈的“杀降”事件。汉高祖刘邦在战争中尽管也有“杀降”行为,却以发表“杀降不祥”观点,并反复谴责项羽“杀降”,表明社会观念有所变化,体现出生命意识的觉醒。主讲人以《史记》中关于汉代将军李广的记载为例,李广曾就自己未能封侯的问题与时人王朔讨论,王朔批评李广曾诱降反羌,诈而杀之,“祸莫大于杀已降,此乃将军所以不得侯者也。”明确表明了反对“杀降”的立场,与刘邦“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语具有一致的价值倾向。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学”盛起,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盛景,秦国也并不例外。主讲人以甘茂、蔡泽等人为例,指出在“兵革为起”、“战国横骛”的战争背景下,战国时人所谓“百家之术”“百家之说”“百家之言”,却都是在说明秦思想史时言及,《史记》中记述战国及秦代文化史时也屡说“百家”,说明“百家思想”在秦国长期以来并非受到简单的绝对的排斥,像法家学说、墨家学说与兵家学说这类实用性的学说仍为秦国王者所积极接受。
在此基础上,主讲人进一步指出,随着秦统一的进程,其文化理念也逐渐发生变化。秦人主张实用主义,对东方“教化仁爱”之学的敌视由来已久,早期《商君书》中所列举“十者”、“六虱”的说法旗帜鲜明地表达出对“礼义德行”的排斥。而到了秦始皇时期,《会稽刻石》中明确出现“咸化廉清”的语句,表明“廉”已经成为当时社会所推崇的品质,由此可以推断出秦文化对东方传统政治文化的逐步接受。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即秦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国耻意识的深化;秦在与东方文化的竞争中逐步洗刷游牧生活传统的遗存;政治道德层面秦文化与东方文化在妥协基点上的融合以及秦帝国执政者对商鞅“刻薄”偏执的行政倾向的修正。
对于秦国的技术发明和生产进步,主讲人再次强调,治秦汉史不能只聚焦于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史学提醒我们关注社会生产力的变化,随后便从水利经营、交通建设、机械发明、动力革命、技术管理五个方面展开分析。主讲人认为,先进的科技是秦国在战国后期实现“不可与战”之优越国力的重要条件之一。
最后,主讲人从长时段的文化史角度对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进行总结,指出秦国对实用之学的高度重视,对实用之学的强势推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得以突出显现。但是另一方面,秦推崇“实用”之学至于极端,简单武断地否定理论性、思辨性的学说,却不利于长久的文化建设和教育进步。
在讲座讨论环节,章义和教授指出,从研究路径上来说,王子今教授在充分掌握传世文献的基础上,还广泛关注、吸收了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和相关成果;而从研究内容上来说,王子今教授提出了过去常为治学者所忽视的许多重要研究方向。随后,王子今教授就同学们所提出的关于秦汉时期齐、鲁文化传统承继、秦代墓葬所体现的社会性质、秦代墓志中的“徒”等问题进行了细致地解答。
002cc白菜资讯融媒体中心
撰稿、摄影:蔡田雨
编辑:王思蕊
投稿邮箱:lsrmtzx2020@163.com

-
-





 冷战史研究中心
冷战史研究中心